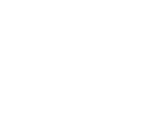智慧城市是为了推进市民参与
在业界,使用新型传感和分析技术来改进城市运作系统的方法一直受到极高的关注,采取这种方法的城市被一些人称作“智慧城市”。与此同时,在这个资源紧缺、自然环境变化的时代,地方政府正想方设法提高工作的效率和适应力。
然而,新技术和政府工作目前还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现状,私营部门就必须退一步。应当意识到,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在整个城市诸多系统中,只是系统之一的一个组件。不管技术发展得多么巧妙,甚至无处不在,都无法脱离政治和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让这些新技术走上另一条路,使其能推进公众参与的进程。
每座城市、每种文化都不相同。香港做出的选择不同于纽约;新加坡有令人羡慕的办事能力;在罗马,生活是甜蜜的……尽管每个地方的背景不同,城市间的共性在于,需要在“自上而下”的官方权威和“自下而上”的社区交流之间找到平衡。智慧城市运用传感器收集数据信息,并对之进行计算处理。一定程度上,数据收集可以促进“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达,公众参与可以影响“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定。智慧城市可以与政治民主平行推进,在“自下而上”与“从上至下”之间更快地找到平衡,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并使城市及其市民能及时应对时代的变化。
管理的要义在于选择
尽管全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尝试“智慧城市”改造,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智慧城市”,目前尚无统一定论。2007年,一群欧洲的学者做了一项研究,给出了“智慧”的6种特点、31个要素、74种指标。最近,欧洲委员会给出的“智慧”定义,不再纠结于定性的标准,而将着眼点放在“智慧”的目的上,认为“智慧”是提升公共服务与降低能耗的有力措施。美国城市规划师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高度关注付诸实践的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将其称作智慧:“城市与通信技术革命联姻”。现实案例有:韩国松岛宣布建立嵌入式通信网络;里约热内卢推出新的“操作中心”,可整理城市各处的信息,将之放到屏幕墙上。
在智慧城市中,指挥和控制是常见的主题。不过,控制设备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控制社会则是政治问题。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说的那样,“管理的要义在于选择”,那些更好的选择,正是智慧城市的要义。
有句话说,城市本是杂乱生长,却总被他者改变。事实上,即便有时市民放弃选择权,城市也总是因其市民的选择而改变。不少人隐约意识到城市积极改变的必要性。然而,更多人对此感到无能为力,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巨大和复杂的问题:城市缺乏政治透明度,即便一个很小的公共项目,也可能需要花费极高成本才能实现。这在那些改变城市的人和那些被城市改变生活的人之间投下了隔阂。或许,智能技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除这道隔阂,提高城市政府决策的效率和准确率,扩大公众参与度。
更具智慧的用地评估
纽约市提出的数字解决方案尽管不像那些智慧城市倡导者想象的那般先进和美好,但纽约对于新开发提案的公共审查程序,足以成为智能技术促进公众参与城市重要进程的一个务实范本。
统一土地利用审查程序(ULURP)是对政府行为许可的特别授命。在每个对纽约城市面貌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的提案中,公众意见都会被提及。这一调节过程源自上世纪60年代那场史诗般的战役:罗伯特·莫塞们(Robert Moses)——这座城市中并非经过选举、却实际掌权的建造者们,“对阵”当时极富影响力的作家、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双方就是否要拆除格林威治村,修建穿过曼哈顿下城的高速公路一事发生激烈辩论。雅各布斯与莫塞公然对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撰写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城市规划的奠基石。ULURP程序重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对峙,在公开听证会上,进行官方投票和听取公众意见这两个程序交替进行,数月之后,双方才能取得妥协并达成一致。
ULURP程序出色地在社区和政府之间取得了平衡,但总体来说,完成这一进程的耗时还是太久。从开始着手准备提案,进入ULURP程序,再到之后面对法院审查,整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十年时间;也就是说,一幢建筑从提出建造方案到真正拔地而起,需要十年时间。一些智慧城市技术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可视化手段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借助可视化技术,城市规划者可免费获取建筑物数字模型,从任一角度观察城市面貌的外在变化,或观看它在某种解决方案之下的变化。每位市民都可点开智能手机中的摄录设备,记录下建筑工地的变化,还能在虚拟环境中观察自己社区即将发生的变化。而现在,他们必须排着队,在预先安排好的听证会上,看着建筑师从预先选定的角度介绍自己未来社区的样貌,不给任何前因后果,没有任何探索空间,这对公众参与而言,无疑是个大障碍。当公众感到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不足,难以做出明智决定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不同意”。于是,整个建造进程就这样被一再延迟。
第二,城市规划者和开发者应该学会评估某个体系对实际生活的影响。要真正理解一个新的城市主要建筑、公园或一处基础设施将怎样影响其所在区域。公共进程要求政府提供一份环境影响力声明,这些声明往往动辄成百上千页,内容枯燥干涩,项目支持者在法院审查中用其证明项目审批过程完全合法,毫无欺瞒隐藏。为什么不借助智能技术将这类公开文件转换为一个设计产品呢?现代技术允许设计师在建造前,得到详尽的各项建筑参数以及涵盖显示环境的可视化模型,再提出切实可行的建造方案。这些建模能够也应当影响建筑设计。当然,这一过程没有理由不公开透明。
下一个挑战:沿海恢复力
对于ULURP程序而言,智慧城市的技术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提高其速度和效率。举个最近的例子,2012年,桑迪飓风给纽约造成了420亿美元损失,洪水把我在布鲁克林红钩区的房子也给冲垮了。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时代,每一个新建筑项目都必须能帮助城市快速适应严峻的新环境。海平面正在上升,那些曾号称“百年一遇”的暴风雨正日益频繁发生。在谈到环境影响问题时,我们不能用“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话草草了事,逃避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构建城市恢复力,而不只是避免使城市遭到伤害。这是纽约即将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另外,全球约有10亿人口居住在沿海城市。
在史蒂文森理工学院,我们成立了“沿海恢复力和卓越城市中心”(the Coastal Resilience and Urban Excellence Center,CRUX)以帮助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主要利用智能技术来采集数据、同公众进行交流、为复杂方法建立模型。
首先,我们试着将“水”纳入智慧城市定义中。我们在纽约各个码头的防洪堤和浮标上装上传感器,建立相应的网络系统,从中采集数据。水流方向、水流速度、含盐度和水位落差,实时显示在高分辨率的网格中。借助这些数据和一个复杂的水动力分析模型,我们预测风和水波之间的相互作用,准确率可达到95%,这使我们有能力了解哪些比较脆弱的高地可能受到风暴潮侵袭。其次,我们通过“智慧霍伯肯”项目(Smart Hoboken),在陆地上也安装了传感器。桑迪飓风带来的洪水曾使2万人滞留于城市。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监测风暴应对能力的网络,提供灾难期间的相关数据,增加日常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的透明度,让所有这些信息向市民和政府官员公开。
最后,我们想为“智慧霍伯肯”项目(Smart Hoboken)建立一个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具备物理学科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作为市民,我们应该如何做决定?自己决定还是共同决定?这个模型就好比是一个游戏引擎,允许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做选择——前提是我们能成功地将这些选择对营建环境造成的影响可视化。这一基于主体的建模形式可以反复运行,每一次我们都能对提出的项目或政策有新的发现。长此以往,这些参数模型本身,因其不断模拟区位划分和建造的方式,就会变成“可供学习的法律”(laws that learn)。运用这些智能技术,在城市重要决策中,人们对一些复杂决议的认可度会明显提高。
回到之前提过的第一点,一座城市属于它的市民。我们决心提高对技术的认识,更多地利用技术,但也绝不会向技术让位。我们要把控好战略决策的方向,并将其落实。
我相信,智慧城市技术最强大的作用,就是能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之前可能从未想过可以成为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而现在他们可以参与政治、经济议题的讨论,为将城市改造得更美好做出决策。简·雅各布斯曾说:“只有当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它的建构进程中时,城市才有能力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些什么。”实际上,只有让城市进程更加透明化、参与度更高,我们才能最终将之践行。
作者:亚历山德罗斯·沃什伯恩(Alexandros Washburn)系史蒂文森理工学院“沿海恢复力和卓越城市中心”(Center for Coastal Resilience and Urban eXcellence,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创始人(来源:澎湃新闻网)
图片使用申明:原创文章图片源自‘Canva可画’平台免费版权图片素材;引用文章源自引用平台文章中所使用的原图。